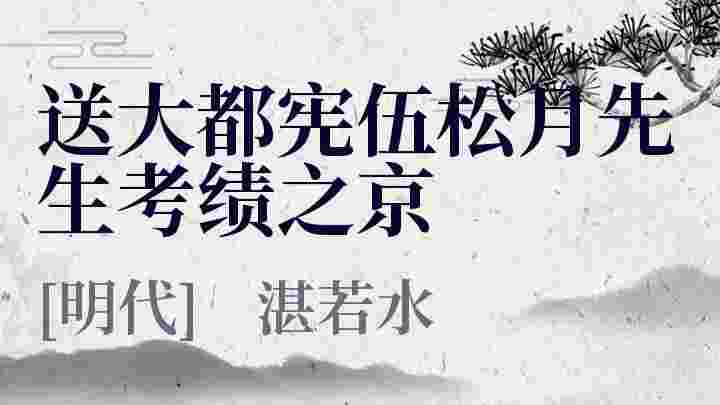猜你喜欢
玉瘦香浓,檀(tán)深雪散。今年恨、探梅又晚。江楼楚馆,云闲水远。清昼永,凭栏翠帘低卷。
坐上客来,尊前酒满。歌声共、水流云断。南枝可插,更须频剪。莫直待西楼、数声羌(qiāng)管。
细细的梅枝,浓浓的梅香,馨香一直持续到雪化。想起赏梅,发现已经过了赏梅时节,只剩下遗憾。寄居在外,路途漫漫。白日如此漫长,倚栏望去。
宴上客人来来去去,杯中满是美酒。歌声唱合,如行云流水。那些最早开花的梅枝要在它们还没开败时,就要多采剪。人身的聚散本是匆匆,独上西楼,听那幽怨的羌笛声。
参考资料:
1、杨合林.李清照集【M】.湖南:岳麓书社出版社,1999.
玉瘦:比喻梅花的清秀之姿。檀:比喻花的香味。恨:遗憾。探:观赏。江楼楚馆:泛指旅舍。云闲水远:形容行程遥远。
南枝:向阳梅枝,最先发花。西楼:指思妇住处。羌管:即羌笛。笛曲中有《梅花落》,甚为凄凉。
上片开门见山,吟咏梅花且叹悔此次赏梅又迟来了一步。梅花,以其寒冬腊月发花,且有坚贞耐寒之志而深受爱重,在我国历来有“国花”之称誉;其花五瓣,花色有白、亦有红;古人赏梅讲究“四贵”,除贵曲不贵直,贵疏不贵密之外,也贵梅花之瘦不贵其肥,贵梅花之合(含苞)而不贵其开(盛放)。“玉瘦香浓,檀深雪散,今年恨探梅又晚”是说:玉色的白梅花清瘦飘逸,浅红色的梅中上品檀香梅相形之下显得色泽浓艳,它们散发着袭人的香气;白雪正在消融,那雪压梅枝的美景已不见;真真令人遗憾,没想到赏梅竟然又来晚了。一个“又”字,表达了词中主人年年探梅、年年叹晚的心情;当然只有面对爱之甚深的对象,才会发出“恨晚”的叹息。此处也足见作者遣词匠心之一斑。
“江楼楚馆,云闲水远。清昼永,凭栏翠帘低卷”之句,交待了赏梅的环境地点、写出了远眺近俯的自然景色,也刻划出了一种闲适恬淡的心境。句中“楚馆”的“楚”字,本指春秋战国时的楚地,即今之湖南、湖北一带,此处泛指江南。在长江之滨的楚地南天,错落矗立着无数亭台楼馆,这里梅花竞放,又是赏梅的好去处;仰望白云闲散依蓝天而飘浮,俯视碧波涟漪逐江水而流逝;清凉的白昼是这样漫长,沉醉在阵阵梅香中的探梅人,凭倚着雕栏放眼远望,信手卷弄着低垂着的翠绿色的帷帘。上片至此而止,主要是侧重写景的幽深、人的安闲,为下片不平静心情的抒发埋下伏笔,达到以静衬动的效果;当然,如果说此处静中伏有波澜的活,便是“清昼永”中的“永”字撩起的。“永”是长的意思,人物感觉上的时间是长还是短,随人的心情而变:欢乐嫌短,愁苦恨长,这是人之常情。那么词中人“清昼永”之说,内里是否包含着几分惆怅。
下片“坐上客来,尊中酒满”两句写的是良友相聚、举杯飞觞、开怀畅饮、纵歌抒怀的场面。“歌声共,水流云断”,充满诗兴豪情的文人雅士对酒自是高歌,面对着象征高雅气节又令人心神陶醉的梅花。于是,群情激动,纵情引吭,你唱我和,这歌声充塞天地、嘹亮悠扬,上遏白云、下断流水。该词至此,欢乐之情已达顶巅,激越的情绪随着歌声止歇渐渐平静下来,另一种心态便代之而起,词人的笔触也宕然转开,回到赏梅的现场“南枝可插,更须频剪”,然后便在“莫直待,西楼数声羌管”的颇怀伤感的声中戛然止住。从字面意思看这几句是指点着眼前的梅树;那南边向阳枝头上的花儿令人喜爱,可以攀折供插,需趁着它方开未残,快多些采剪,或簪在鬓边,或插放几案,把梅的疏姿倩影和梅的寒香冷艳尽多的留在身边;千万不要等到花瓣残落、随风化泥的时刻再惆怅留连。弦外之音却是借物抒情,感伤光阴流逝,花开花落,容颜易老,聚少离多,人生得意与相聚之时需尽情欢畅,待到《梅花落》的曲调已经奏起,羌笛声声泣诉别离的时候,离愁别怨便会铺天盖地地袭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