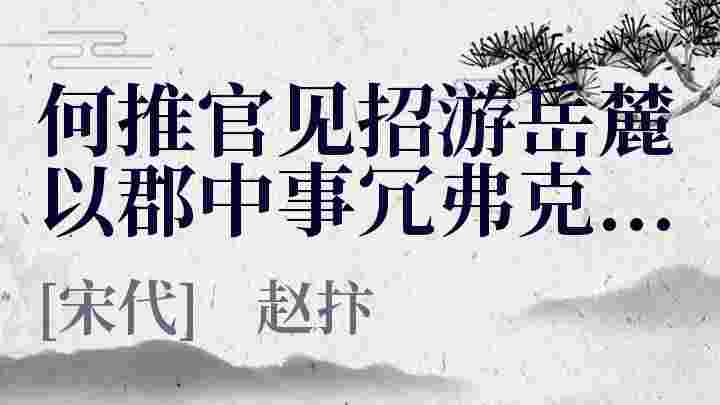猜你喜欢
第一折
(冲末扮太白星官引青衣童子上,云)吾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。奉上帝敕命,遣临下界,纠察人间善恶。有天台山桃源洞二仙子,系是紫霄玉女,只为凡心偶动,降谪尘寰。又见天台县刘晨、阮肇,此二人素有仙风道骨,向因晋室衰颓,奸谗窃柄,甘分山林之下,修真练药,以度春秋。今日必上天台山采药,不免将白云一道,迷其归路。却化一樵夫,指引他到那桃源洞去,与二仙子相见,成其良缘,多少是好。但可惜刘、阮二人尘缘未断,终有思归之心,那时节我再度他,未为晚也。正是平空舒出拿云手,指引山中采药人。(下)(正末扮刘晨,外扮阮肇,各带砌末上,云)某姓刘名晨,这位兄弟姓阮名肇,俱系天台县人氏。幼攻诗书,长同志趣。因见奸佞当朝,天下将乱,以此潜形林壑之间,无志功名之会。现在天台山下,盖一所茅庵,与兄弟修行办道。岂不闻圣人之言: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,倒大来达时务也呵!(唱)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啸傲烟霞,寸心休把名牵挂。暗里年华,青镜添白发。
【混江龙】山间林下,伴药炉经卷老生涯,眼不见车尘马足,梦不到蚁阵蜂衙。闲来时静扫白云寻瑞草,闷来时自锄明月种梅花。不想上书北阙,不想去待漏东华。似这等鲲鹏掩翅,都只为狼虎磨牙。怕的是斩身钢剑,愁的是碎脑金瓜。怎学他屈原湘水,怎学他贾谊长沙。情愿做归湖范蠡,情愿做噀酒栾巴。携闲客登山采药,唤村童汲水烹茶。惊战讨,骇征伐;逃尘冗,避纷华;弃富贵,就贫乏。学圣贤洗涤于是非心,共渔樵讲论会兴亡话。羡杀那知祸福塞翁失马,堪笑他问公私晋惠闻蛙。
(阮肇云)兄长,时当春暮,我和你上天台山去采种药苗。似这景物,真堪玩赏也。(正末唱)
【油葫芦】一上天台石径滑,践翠霞则见这竹篱茅舍两三家,听得那夕阳杜宇啼声煞,这时节春风桃李花开罢。我虽不伴长沮事耦耕,学严陵理钓槎。常则是杖头三百青钱挂,抵多少坐三日县官衙!
【天下乐】也算个闲趁东风数落花,荣华,谁恋他?敢则是瓦盆边几场沉醉杀。快清风,袍袖宽,倦红尘路径狭,便休题相逢不下马。
(云)登高履险,不觉困倦,就此松阴之下,拂石而坐,少憩片时。(做坐科,阮肇云)我和你在山林下修行,不过穷居野处,升高望远。想那朝中为宫的利泽施于天下,声名流于后世,其间孰得孰失,兄长所见若何?(正末云)兄弟,那为官的到底不如我闲居的好。(唱)
【那吒令】朝廷内,怨煞荐贤的叔牙;林泉下,傲煞操琴的伯牙;磻溪上,老煞钓鱼的子牙。人情似啖马肝,世味如嚼蜂蜡,叹纷纷尘事抟沙。
【鹊踏枝】远奢华,近清佳,火炼丹砂,水煮黄芽。牢拴住心猿意马,急疏开利锁名枷。(阮肇云)这几年天下荒荒,干戈并起,不能勾风尘宁静。若有英雄生于此时,觑事业如拾芥耳。(正末云)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,其次避色,其次避言。兄弟,还只是我们的见识高得多哩。(唱)
【寄生草】我情愿弃轩冕离人世,傍泉石度岁华。一任他英雄并起图王霸,烟尘并起兴戈甲,异端并起伤风化。我和你韬光晦迹老山中,煞强如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(太白扮老人上,云)那刘、阮二人来了,吾先使白云一道,迷其归路,化作樵夫,立于路傍,他二人必来问路,却指引他到桃源洞去借宿,岂不与二仙子相遇?(正末同阮做起行科,云)兄弟,天色渐晚,药苗已采,便可下山回家去罢。(唱)
【幺篇】去去山无尽,行行路转差。则为那白云渐渐迷高下,不由咱寸心悄悄耽惊怕,见-个村翁远远来迎迓。我这里为迷山路问樵夫,抵多少因过竹院逢僧话。
(做见科,太白云)贤者何由经此?(正末云)俺兄弟二人上山采药,信步游玩至此。(唱)
【醉中天】信脚山之下,洗耳水之涯。正失路迷踪没乱煞,(带云)得遇老人呵,(唱)抵多少卖得龟儿卦。(太白云)二位可通个姓名,现居何处?(正末唱)我两个本东庄措大。(太白云)我看你二位生得齐整,像个出仕的人。(正末唱)休认做名题科甲,(太白云)二位可还有甚陪伴的么?(正末云)若问我陪伴的呵,(唱)无非是糜鹿鱼虾。
(云)小生姓刘名晨,兄弟姓阮名肇,现在天台山下闲居修行。(太白云)二位既是修行,每日在山中,有甚生涯过遣?(正末唱)
【金盏儿】你问我甚根芽,甚生涯。我那里看家猿鹤年高大,当门松桧树槎枒。常则是道书堆玉案,仙帔叠青霞。端的个山中闲宰相,林下野人家。(太白云)我看二位都是读书君子,方今圣朝以贤良方正取士,二位不去求名应举,却是隐遁山林,为着何来?(正末云)小生与兄弟慕山林幽雅,遂有终焉之意。那为官的,我怎么学他。(唱)
【后庭花】并不想有轩车有驷马,我则愿无根椽无片瓦。出来的一品职千钟禄,那里有六韬书三略法,他都是井中蛙妄称尊大。比周公不握发,比陈蕃不下榻。空结实花木瓜,费琢磨水晶塔。斗筲器不足夸,粪土墙容易塌,儿童见惊讶杀。
【青歌儿】空一带江山、江山如画,止不过饭囊、饭囊衣架,塞满长安乱似麻。每日价大纛高牙,冠盖头踏。人物不撑达,服色尽奢华,心行更奸猾。举止少谦洽。纷纷扰扰由他,多多少少欺咱,言言语语参杂。是是非非交加。因此上不事王侯,不求闻达。隐姓埋名做庄家,学耕稼。
(太白云)二位,此处到山下,还有数里之遥,天色已晚,若归去恐为狼虎所伤。兀的看山那搭,红轮直下,有个桃源洞人家,可投宿一宵去。(正末举手做谢科,云)多谢指引。(唱)
【赚煞】投至的山上采芝回,早难道江上踏青罢,眼见得路迢遥芒鞋邋遢。抵多少古道西风鞭瘦马,叹明朝回首天涯。谩嗟呀,那里也出入通达,不觉的枯木寒烟噪晚鸦。望青山那搭,红轮直下,兀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。(同阮下)
(太白云)吾指引他二人往桃源洞去了也,别遣青衣小童,报知二仙子,与他成此夙缘。(诗云)寻真不觉路迢遥,蚤见斜阳转树梢。咫尺洞天风景异。碧桃花下凤鸾交。(下)
第二折
(二旦扮仙子引侍女上,云)子童二人,乃上界紫霄玉女,偶因有罪,降谪人间,现居天台山桃源洞中。今经日久。有太白星官命青衣童子来报,说目下有天台县刘晨、阮肇二人,与子童有五百年仙契,今来采药,必当相会。不免分付侍女们,安排酒果,亲自出洞迎接去咱。(正末同阮肇上,云)不想入山采药,盘桓日夕,竟被白云迷其归路,遇一樵夫指引,去桃源洞人家寄宿一宵。行来数里,尚未得到。兄弟,似此路径,登高涉险,索受艰苦也呵。(唱)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风力紧羽衣轻,露华湿乌巾重。我本为厌红尘跳出樊笼,只待要拨开云雾丘陇,身世外无擒纵。
【滚绣球】香渗渗落松花把山路迷,密匝匝长苔痕将野径封,静巉巉锁烟霞古崖深洞,高耸耸接星河峭壁山赞峰,闹炒炒栖鸦噪暮天,悲切切玄猿啸晚风。絮叨叨鹧鸪啼转行不动,碜磕磕踞虎豹跨上虬龙。白茫茫遍观山下云深处,黄滚滚咫尺人间路不通,眼睁睁难辨西东。
【倘秀才】我待学炼九转丹砂葛洪,上万丈昆仑赤松,因此上思入风云变态中。(云)兄弟,你看一溪流水,几片落花,这山中必有人家也。(唱)则见一溪流水绿,几片落花红,兀的把春光断送。(云)兄弟,这般景物,畅是宜人,我且题咏几句咱。(阮云)兄长正好题咏几句,小弟拱听。(正末唱)
【滚绣球】水呵莫不黄河天上来?花呵莫不碧桃天上种?水呵索强如翠岩前三千丈玉泉飞进,花呵干闪下闹西园一队队课蜜游蜂。水呵则是弥漫三月雨,花呵可惜狼藉一夜风。水呵近沧波濯尘缨一溪光莹,花呵性轻薄乱飘零枉费春工。水呵抵多少长江后浪催前浪,花呵早则一片西飞一片东,岁月匆匆。
【倘秀才】我这里长啸时草木振动,怅望处风涛怒涌,不觉的悄然而悲悚然恐。(阮肇云)咱两个则傍这一道流水寻去,料的前面必有个渔家可以投宿。(正末唱)盼不的渔家春水渡,(阮肇云)这山中敢有个寺儿么?(正末唱)闻不见僧寺夕阳钟,(带去)兄弟呵,(唱)咱两个莫不被樵大调哄?
【滚绣球】我这里度危桥柱瘦筇,俯清流靠古松,(云)兄弟,你看水上流出一杯饭来了。(唱)见一杯胡麻饭绿波浮动,(做取,分食科)(唱)想行厨只隔云峰。进程途一二里,见楼台三四重,势嵯峨走鸾飞凤,晃分明金碧玲珑。(内做奏乐科,正末云)这是甚么响?(唱)又不是数声仙犬鸣天上,又不是几处樵歌起谷中,(带云)待我听咱,(做听科)(唱)只听的环珮丁冬。
(二仙子引侍女,将砌末上,云)刘晨、阮肇二人已到了。不免引着侍女,将酒礼乐器出去迎接着。(正末做见科)(诗云)天和树色蔼苍苍,霞重岚深路渺茫。云窦满山无鸟雀,水声沿涧有笙簧。碧纱洞里乾坤别,红杏枝头日月长。愿得花间有人出,免教仙犬吠刘郎。兄弟,你看霞光凤驭,羽盖霓旌,笙歌缭绕,珠翠妖娆,这都是那里来的?(阮肇云)是好跷怪!好跷怪!(正末唱)
【呆骨朵】你便铁石人也惹起凡心动,莫不是驾青鸾天上飞琼?似这般花月神仙,晃动了文章巨公。(做相见科,旦云)刘郎、阮郎,请同到舍下。(正末云)他女娘家怎知我们的名姓,便以刘郎、阮郎呼之?兄弟,我和你莫非是梦中么?(唱)没揣的撞到风流阵,引入花胡同。摆列着金钗十二行,敢则梦上他巫山十二峰。
(做行到科)(正末云)到这境界,分外幽绝,令人翩翩然有出尘之想。不知生等何缘,得至于此?(唱)
【脱布衫】光闪闪贝阙珠宫,齐臻臻碧瓦朱甍。宽绰绰罗帏绣栊,郁巍巍画梁雕栋。
【醉太平】注金波碧筒,烧银烛纱笼,笙歌引至画堂中,红遮翠拥。人心此会应相重,人情今夜初相共,人生何处不相逢?早忘却更长漏水。(二旦做意把盏科,云)草草杯盘,不足以待贤者,惶恐!惶恐!(正末谢云)生等不才,多承错爱,何以克当?(唱)
【倘秀才】则见他喜孜孜幽欢密宠,便一似悄促促私期暗通,怎消得翠袖殷勤捧玉钟?屏开金孔雀,褥隐绣芙蓉,兀的般受用。
(小旦扮金童、玉女上,云)咱两个奉王母仙旨,将这仙桃来献桃源洞二仙子,兼贺得婿之喜。(正末云)兄弟,这话那里说起?(阮肇云)兄长岂不闻酒中得道,花里遇仙,也是常事?(正末唱)
【滚绣球】真乃是罗绮丛,锦绣中,出红妆主人情重,玳筵开炮凤烹龙,受用些细腰舞皓齿歌,琉璃钟琥珀醲,抵多少文字饮一觞一咏,列两下进仙桃玉女金童。不觉的舞低杨柳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,筵宴将终。
【叨叨令】记不的轩辕一枕华胥梦,学不的淳于一枕南柯梦,盼不的文王一枕非熊梦,成不的庄周一枕蝴蝶梦。倒大来福分也么哥,倒大来福分也么哥,恰做了襄王一枕高唐梦。
【三煞】帽檐偏侧簪花重,衫袖淋漓污酒浓。品竹调丝,移商换羽;掿粉搏酥,走斝飞觥。一个个浓妆艳裹,一对对妙舞清歌,一声声慢拨轻拢。赢得我忘怀昆仲,拚却醉颜红。
【二煞】一杯未尽笙歌送,两意初谐语话同。效文君私奔相如,比巫娥愿从宋玉,似莺莺暗约张生,学孟光自许梁鸿。他年不骑鹤,何日可登鳌?今夜恰乘龙。说甚的只鸾单凤,天与配雌雄。
【随煞尾】色笼葱光潋滟,山环水绕天台洞。势周旋,形曲折,虎踞龙盘仙子宫。本意闲寻采药翁,谁想桃源一径通。谩叹人生似转蓬,犹恐相逢是梦中。月满兰房夜未扃,人在珠帘第几重。结煞同心心已同,绾就合欢欢正浓。焚尽金炉宝篆空,烧罢银台烛影红。身在天台花树丛,梦入阳台云雨踪。准备着凤枕鸳衾玉人共,成就了年少风流志诚种。(同下)
楔子
(小旦上,云)小妾是桃源洞仙子侍从的。为刘晨、阮肇二人,与俺仙子有五百年夙世姻缘,自去春与仙子成了姻眷,到今刚及一载。奈二人尘缘未断,又早思归。今日令我等先将酒果到十里长亭伺候,待仙子与刘阮相别。(正末同阮肇、二旦乘车上,云)咱兄弟二人自去春到桃源洞中,多感二位小娘子错爱,倏忽一载。且莫说他温香软玉,恩意绸缪,只是绣阁兰房,尽也受用不尽。怎奈心中只想回归乡里,目今又值暮春时候,闻得百禽鸣野,使我思归之意,一倍加切。不免暂时告别回家,小娘子休得见怪。(二旦做打悲科,云)我二人自谓终身已得所托,刚才一载,乃遂别乎?常言道:心去意难留。贱妾便当相送,亲至十里长亭,一杯饯别。(做把酒科)(正末回酒科,旦云)贱妾聊赋一诗相赠。(诗云)殷勤相送出天台,仙境那能却再来?云液既归须强饮,玉书无事莫频开。花当洞口应长在,水到人间定不回。惆怅溪头从此别,碧山明月照苍苔。(正末云)多谢小娘子厚意,这般眷恋。但此别非久,不过旬日之间便当再会也。(唱)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我做甚三叠阳关愁不听,也只为一段伤心画怎成。则不是人感慨别离轻,听兀那流莺树顶。先啼出断肠声。
【幺篇】抵多少绿暗红稀出凤城,拚得个倒尽沙头双玉瓶。直到这十里短长亭,避不的登山蓦岭,便子索回首问前程。(正末同阮下)
(旦云)他二人去了也。我等本待和他琴瑟相谐,松萝共倚,争奈尘缘未断,蓦地思归。虽然系是夙因,却也不无伤感;倘若天与之幸,再与他相见,亦未可知。(诗云)人间无路水茫茫,玉洞桃花空自香。只恐韶光易零落,何时重得会刘郎?(并下)
第三折
(净扮刘德引沙三、王留等将砌末上,云)某姓刘名德,现在天台县十里庄居住。时当春社,轮着我做牛王社会首。今日请得当村父老、沙三、王留等,都在我家赛社。猪羊已都宰下,与众人烧一陌平安纸,就于瓜棚下散福,受胙饮酒。牛表伴哥,你把柴门紧紧的闭上,倘有撞席的人,休放他进来。(众做打鼓、烧纸、饮酒科)(正末同阮肇上,云)自到桃源洞中与那两个小娘子结成姻眷,不觉过了一载。为闻百鸟鸣春,顿起思归之念,再寻旧路回家。兄弟,你也看见,这眼前景物都更变不同了,好伤感人也呵。(唱)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兔走乌飞,搬不尽古今兴废,急回来物换星移。成就了凤鸾交,莺燕侣,五百年夙缘仙契。不多时执手临岐,倒揽下干相思一场憔悴。
【醉春风】则被这红灼灼洞中花,碧澄澄溪上水,赚将刘阮入桃源,畅好是美,美。受用他一段繁华,端详了一班人物,别是个一重天地。
(做行路科,阮肇云)兄长,这一路上全不似旧时光景,却是何故?(正末唱)
【迎仙客】下坡如投地阱,蓦岭似上天梯,这的是蝴蝶梦中家万里。不甫能雨才收,没揣的风又起。似这般风雨凄凄,早难道迟日江山丽。
【红绣鞋】见了这三五搭人家稀密,过了这百千重山路逶迤,那里也新郎归去马如飞。愁的是林深禽语碎,怕的是路远客行迟,呀!却原来鹧鸪啼烟树里。
(云)早来到这里,望见那古寺,过了一座小桥,便是家中了也。(唱)
【醉高歌】望见那萧萧古寺投西,行过这泛泛危桥转北。早来到三家疃上熟游地,这搭儿分明记得。(正末做意惊见科,云)好怪,这两株松树我去时亲手栽下,与兄弟上天台山采药,到今只有一年光景,这两株树怎么就长得偌来大,不由我心中好生疑惑。(阮肇云)我也记得,这等大的快,敢则是地肥哩。(正末唱)
【普天乐】曾得个几星霜,多年岁,为甚么松杉作洞,花木成蹊?往时节将嫩苗跑土栽,今日呵见老树冲天立。见了这景物翻腾非前日,不由人几般儿心下猜疑。修补了颓垣败壁,整顿了明窗净几,改换了茅舍疏篱。
(做打家唤门科)开门咱,我来家了也。(净云)果有撞席人来,休开门。(正末唱)
【石榴花】则见这野风吹起纸钱灰,咚咚的挝鼓响如雷。原来是当村父老众相知,赛叶王社日,摆列着尊愚。(做叫云)刘弘,开门来,开门来。(唱)到的这柴门前便唤咱儿名讳,他那里默无声弄盏传杯。一个个紧低头不睬佯妆醉,方信道人面逐高低。
【斗鹌鹑】我今日衣锦还乡,儿呵你也合开门倒屣。(云)刘弘,快开门来。(净云)你则是个撞席的馋嘴,怎么敢叫刘弘?要讨我打你。(正末唱)我这里道姓呼名,他那里嗑牙料嘴。则道是餔啜之人来撞席,饕餮他酒共食。似恁般妄作胡为,敢欺侮咱浮踪浪迹。(净云)今日当村众父老在我家赛牛王社,烧一陌纸,祈保各家平安。那里走将这两个不知羞耻的人来,要我酒肉吃,倒魇镇俺众人一年不吉利。(正末唱)
【上小楼】则见他一时半刻,使尽了千方百计。吃紧的理不服人,言不谙典,话不投机。看不的乔所为,歹见识,刁天决地,早叹道气昂昂后生叮畏。(净云)这等撞席的人,倒敢胡言乱语的。牛表、沙三,急忙打出去者。(众做打科)(正末唱)
【幺篇】真乃是重色不重贤,度人不度己。使的这牛表、沙三、伴哥、王留,唱叫扬疾。走将来手便棰,脚便踢,将咱忤逆,这的是孩儿每孝当竭力。(云)我是刘晨,同兄弟阮肇去春上天台山采药,今年归家。你是何人,倒来打我?(净云)你这两个面生可疑之人,我那里认的?你快去!快去!(正末唱)
【满庭芳】你道我面生可疑,便待要扬威耀武,也合问姓甚名谁。那些个吐虹霓三千丈英雄气,全不管长幼尊卑。(净云)我父亲刘弘在日,尝说老爷刘晨,上天台山采药不归,到今百余年,知他是狼餐豹食?你还提他则甚?(正末唱)你道我上天台狼餐豹食,谁想我入桃源雨约云期。休得要夸强会,瞒神吓鬼,大古里人善得人欺。
(净云)这两个汉子是风魔,是九伯。我记的父亲在日对我说,老爷刘晨上天台采药,那一年亲手栽下门前这两株松树,到今百余年,兀那松树长的偌大,我父亲刘弘也故许多年了。你道是上春采药去的,你则看这树,难道一年便长得这般大小?(正末做省悟科,云)则这句话可将我提省了也。我适才到得门首,见这两株树,便觉有些疑惑。这等看来,当真去百余年了。孩儿,此非汝的罪过也,则是我的愚浊。方知道山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,信有之也。(唱)
【十二月】叹急急年光似水,看纷纷世事如棋。回首时今来古往,伤心处物是人非。若不游嫦娥月窟,必定到王母瑶池。
【尧民歌】呀!生折散碧桃花卜凤鸾栖,端的个人生最苦是别离。倒做了伯劳飞燕各东西,早叹道有情何怕隔年期。伤也波悲,登高怨落晖,添几点青衫汨。
(正末做打悲科,云)你父亲刘弘已死,你又是他孩儿,却是我一家骨肉。我当年同兄弟阮肇上天台山采药,只为日暮迷其归路,遇一樵者,指引到桃源洞去投宿。行至数里,忽见金钉朱户,似王者之居。有笙歌一部,簇拥二女子,迎接我二人到家筵宴,成其夫妇。刚及一载,为闻百鸟鸣春,思归故里,早已物换星移,过了一百多岁。信知彼处乃是神仙之境。(阮肇云)兄长,这等看来,我和你便不归家也罢了。(正末唱)
【耍孩儿】方信道洞天深处非人世,包藏着云纵雨迹。(带云)我想临行之时,(唱)怎将断肠诗句赠别离,分明是漏泄与肉眼愚眉。他道花当洞口应长在,水到人间定不回。参透了其中意,本是个神仙境界,错认做裙带衣食。
(净云)听了你这一篇话,你敢真是俺老爷,做了神仙回家来的。老爷,则你一向在那里受用?(正末唱)
【五煞】我受用淡氤氲香喷鹊尾炉,光潋滟酒倾蕉叶杯。脚趔趄佳人锦瑟傍边立,醉疏狂闲吟夜月诗千首,眼迷希细看春风玉一围。到今日归何地?想杀我龙肝凤髓,害杀我螓首蛾眉。
【四煞】也曾交颈睡并手行,也曾重裀坐列鼎食。不枉子百年三万六千日,依旧索背将宝剑匣中去,再也不倒着接篱花下迷。成就了风流婿,匹配上鸾交凤友,差排下蝶使蜂媒。
【三煞】他那里一壶天地宽,两轮日月迟,不比这彩云易散琉璃脆。但不知别来仙子今何在,从今后逢着仙翁莫看棋。回首更人世,我只怕泰山石烂,沧海尘飞。
【二煞】现如今桃源好结缡,问甚么瓜田不纳履,我和他武陵溪畔曾相识。寂寞了十二阑瑶台仙子吹箫伴,迢递了五百里芳草王孙去路迷。阑珊了三千年王母蟠桃会,生疏了日边蓖翠鸾丹凤,冷落丁云外鸣玉犬金鸡。
【尾煞】折末你奔关山千百重,进程途一万里。我则怕春光去了难寻觅,(云)兄弟,咱和你去来。(唱)趁着这几瓣桃花半溪水。(同阮肇下)
(净云)不想我老爷刘晨,果然遇仙回来,已经隔世,方悟彼处非凡,急急的与阮肇复入山中去了。虽然如此,我又不认的他,知道是真是假?也不必去追寻他了。只是我这牛王社父老每不曾劝的酒,如何是好?(众云)今日天气又好,酒席又盛,虽则被那两个撞席的搅扰了这一会,然也吃得醉的醉了,饱的饱了,我们都散罢,待明年容在下还席。(并下)(净云)父老每都散了也。这两个毕竟是甚么人?非是俺喃喃笃笃,争奈他面生不熟。也不知这刘晨果然是俺爷爷也,又不知那阮肇当真是俺叔叔。又没处辨他假真,任去来不须追逐。纵然在桃源洞炼药烧丹,只不如俺牛王社醉酒饱肉。(下)
第四折
(太白引青衣童子上,云)当日刘晨、阮肇二人上天台山采药,吾以白云一道,迷其归路,化一樵者,指引入桃源洞中,与二仙子成就良缘。惜乎二人尘缘未断,各动思乡之念。比及回家,已经隔世,方悟仙凡有异。如今他再入山中,寻访桃源,渺无踪迹。不免显示真像,指引他到洞,再与二仙子相会,也是我救度他山世超凡的好事。必须先遣青衣小童去那洞中报知仙子,出来迎接他。道犹未了,那刘、阮二人早到。(正末同阮肇上,云)自家与阮家兄弟急到山中访那桃源洞,往往来来,再不得其旧路。怎能勾与二仙子相见,岂非缘薄分浅,致有今日也呵!(唱)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满襟情沿湿青袍,伴离人一竿残照。行不上岩峦临涧绝,盼不到宫阙倚天高。一弄儿行色萧条,恰便似游仙梦撒然觉。
【驻马厅】四顾寂寥,绿树依依云渺渺;一声长啸,青山隐隐水迢迢。看花长在洛阳桥,休官不止长安道。归路杳,也是我寻真误入蓬莱岛。
【沈醉东风】成就了东床婿伏低做小,宴会了西王母接贵攀高。引动这撩云拨雨心,想起那闭月羞花貌。撇的似绕朱门燕子寻巢,没来由北往南来走一遭,眼见的离多会少。
(做行科,云)兄弟,我和你走了这半日,但见高山流水,竟不知那桃源洞却在何处。(阮肇云)敢这桃源洞也似竹林寺有影无形的。(正末唱)
【殿前欢】不觉的五魂消,则见这无媒径路草萧萧,急煎煎似上蚰蜒道。一会价心痒难揉,这时节武陵溪怎暗约?桃花片空零落,胡麻饭绝音耗。做了个云迷楚岫,水淹蓝桥。
(做叹科,云)这等寻来寻去,杳无踪迹,使我进退无门,如之奈何?兄弟,我和你共赋一诗,聊以自遣。(阮肇云)兄长请先倡。(正末诗云)再到天台访玉真,青苔白石已成尘。笙歌寂寞闲深洞,云壑萧条绝旧邻。(阮肇诗云)草树总非前度色,烟霞不是往年春。桃花流水依然在,不见当时劝酒人。(正末唱)
【雁儿落】也是我一事差百事错,空惹的千人骂万人笑。本则合暮登天子堂,没来由夜宿袄神庙。
【得胜令】这的是人怨语声高,我今日得命也无毛。吉丁当掂碎连环玉,生可擦分开比翼鸟。梦断魂劳,身未到心先到;分浅缘薄,有上梢没下梢。(二末做投崖科)(太白现像,急喝云)刘晨、阮肇,休胡寻思。吾乃上界太白金星。为你二人与桃源仙子有夙世姻缘之分,你前日采药迷路,吾曾化为樵夫,指引入洞。今复来此,迷其旧路,听吾指引。(正末同阮拜科,云)愚民肉眼,不识大仙,只望垂悯,指示前路。(唱)
【沽美酒】怎肯学鲲鹏飞杂燕雀,芝兰长混蓬蒿,可正是忙处人多闲处少。早着我迷踪失道,无处访旧时樵。
【太平令】但得你天公指教,抵多少晏平仲善与人交。你若肯扶倾济弱,我可便回嗔作笑。一会价记着想着念着,(带云)休道是人呵,(唱)马也有垂缰之报。
(太白云)那前面桃花开处,兀的不是洞门。你两个此一去,休得忘了大道,只待功行完日,同登天府。(正末同阮谢科)(唱)
【落梅风】过了这苍苔径独木桥,路崎岖寂无人到。刘郎这回归去了,乱山头杜鹃休叫。
【甜水令】元来是路转峰回,林深树密,猿啼虎啸,知他在何处教吹箫。(二旦引侍从、仙乐上科,正末唱)猛见这香雾空濛,祥云缥缈,瑞烟笼罩,还怕咱没福堪消!
(二旦云)不意今日又得相会也。(正末唱)
【折桂令】依然见桃源洞玉软香娇,一队队美貌相迎,一个个笑脸擎着。今日也鱼水和谐,燕莺成对,琴瑟相调。玉炉中焚宝篆沈烟细袅,绛台上照红妆银蜡高烧。人立妖娆,乐奏箫韶。依旧有翠绕珠围,再成就凤友鸾交。
(太白云)众仙近前,听我嘱咐:(词云)紫霄仙谪来人世,修真在桃源洞内。有刘阮共慕清虚,厌浮荣甘心韬晦。当暮春采药入山,与二女夙称仙契。被白云迷失归途,吾指引蓦然相会。成就了两姓姻缘,完结了百年伉俪。甫一岁二子思家,尘缘重凡心未退。急归来物换星移,访子孙已更百岁。见门前小树参天,方省悟仙凡有异。再来时路径全非,何处认旧游之地?又是吾指引来归,神仙眷依然匹配。三年后行满功成,赴蓬莱同还仙位。
题目太白金星降临凡世
紫霄玉女夙有尘缘
正名青衣童子报知仙境
刘晨阮肇误入桃源